界格亦稱“界欄”、“格眼”,或者“邊欄”,這是明代萬曆年間印學家徐上達在其《印法參同》中使用的概念。界格作為一種特有的印面劃分形式出現於印章之中,並非始於秦代。但其在秦印階段卻發展到一個高峰,成為秦代印章最為顯著的形式特徵。

狹義的秦印概念是指秦統一之後到秦滅亡的這十五年間製作的印章,但秦統一後雖然遺留了大量的刻石、度量衡、詔版銘文等,但就流傳至今的秦印實物來看,因無款識紀年,很難斷定其確切年代。即便是秦十五年間墓葬中出土的印章,其墓主人早年生活在戰國時期,所以印章仍然有可能是製作於戰國時期的。在考古學上把統一前後的秦明確的劃分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認為秦印應包括秦統一六國前以及秦滅亡直至西漢初期的數十年在內。羅福頤先生在《近百年來對古璽印研究之發展》[1]一文中說:“秦漢私印之斷代,今日我們的秦印標準是根據秦權量上文字書法來斷定的。”王人聰先生在《秦官印考述》[2]中說:“秦印分官印私印兩大類,秦官印的辨別,除了根據印文字體的特點之外,還可以通過印文所屬官名、地名沿革的考證來確定。”這些方法為斷定秦印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廣義的秦印概念有利於本文研究的深入展開。
1印章界格印式的由來
1.1秦之前璽印界格印式分析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印章實物是著名的三方 “商代璽印”,(圖1、圖2、圖3)原印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學術界經過多年的真偽、時限、屬性等方面的討論和考證,已有相當多的考古學家和研究者認定這三方璽印出自殷商時代。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容庚等人確認其為商代之物並進而對印中釋文進行破譯。當代學者徐暢《商璽考證》一文在總結前賢之說的基礎上,以三方銅璽紋樣與大量有同樣或類似紋樣的商代青銅禮器、樂器、兵器、食器以及甲骨文、商金文作對照研究,力圖破譯三方銅璽的印文、考證其性質、具體時期及使用者的身份。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在《中國璽印的起源》[3]中進一步確認這三方銅璽為“商代古璽”。他在接受《中國書法》(2001年第10期)特約訪談時說:“商代有璽印,過去在安陽出土的,現藏台灣的那三方,至少有二方沒什麼問題,這個我親眼看過。現在西周、春秋璽印也找到了一些。”在2001年第12期《中國書法》上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試說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再一次證實這三方身為平板狀、面正方、背中央有半環形鼻鈕的銅璽絕非偽作,並得出商代晚期確實已有璽印的結論。在隨後的兩周乃至戰國時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帶有界格樣式的印章,如戰國時期楚系鑄印“連尹之璽”(圖4)、戰國齊系鑄印“東武城攻師鈢”(圖5)等,只是此時界格印式沒有普遍成為這些時期印章的主要特徵和主流印式。由此可見,秦代印章的界格印式並不是秦朝原創,而是對先前印式的沿襲繼承和發揚光大。

圖1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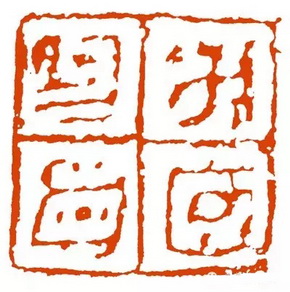
圖3

圖4 連尹之璽

圖5 東武城攻師鈢
1.2秦印選擇界格印式的必然[1]
秦印選擇界格印式還不如說是界格印式遭遇了秦印。這種特殊的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文字和審美的,政治和文化的,施用和驗證的等多重屬性,理所當然的成為大秦帝國中央集權統治印證體系的首選。界格印式廣泛施用於白文印章,成為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印章特徵,並發展成為印章史上的一座高峰,是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的。
1.2.1秦篆文字的形體特徵是界格有無的內在動因
在中國印章史中,不同時期的文字形體與實用印章均有着高度的形態對應關係。文字形體是入印的重要因素,其演變的結果在某些方面直接影響和決定了當時實用印章的發展,左右着印面形式的變化。
戰國時期,秦國地處關西,經濟文化的發展較之同一時期其他各國相對緩慢,其文字形體大體上沿襲了周代的正體文字。秦統一之後,將戰國時期其他六國不同的字體進行一番清整和梳理,在先秦“籀書”文字的基礎之上由丞相李斯等人對其進行省改加工,整理出後來通行的文字“秦篆”,即小篆。唐代張懷瓘《書斷》卷上云:“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2]清代劉熙載《藝概》五《書概》說:“秦篆簡直,如《嶧山》、《琅琊台》等碑是也”。[3]秦篆文字從“增損大篆”中來,其“簡直”的古文字構形更趨符號化,亦少了商周古文字的圖案化。符號化更方便從審美角度來演繹秦篆的軸對稱和上緊下松的外部特徵。在印文上表現為圓轉流暢,凡縱向筆畫皆向下舒展,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筆半行橫折下曳,如戰國時期秦國印章“工師之印”(圖6),先秦印文字固有的特點非常明顯。秦篆文字在分割橫向空間時,從上到下,每一段空間的安排都嚴格遵守等距離的原則,然而在分割到最後一段時,一般情況下都留出較為寬綽的空間,由此出現上緊下松的結體特徵。漢字結構的重量感要比下半部分大,假如上下兩部分空間相等的話,或上大下小的話,都會有頭重腳輕的感覺;只有上緊下松才會感覺重心平穩,有平衡感,同時有一種引體向上的上升感。秦篆文字在橫豎相交的轉折處,全部化方形為圓弧,使得粗細相等的線條婉轉流暢起來,產生流線型的“圓而通”的運動效果。

圖6 工師之印
界格的施用較為合理的解決了秦印文字中上密下疏和文字所佔空間不等的疏密矛盾。秦篆文字的圓勻婉轉與印章方整的邊欄及界格的組合,達到了方圓兼濟,方圓互補,使印面布施更具藝術化。界格與秦篆文字和諧地融為一體,形成了秦印特有的藝術風格。“方”與“圓”是中國傳統美學範疇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着諸多關於方圓學說的論述,此不贅言。圓形的小篆字體和方正的界格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符合美學特徵的。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將秦代文字分為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八體,但其中大多數都是以小篆作為基礎的,只不過是依託文字的載體有所不同而已。其中摹印篆就是指秦印中使用的文字。由於秦篆文字特有的結構特徵決定了以界格作為這一時期印章的主要特徵。當秦摹印篆演變為後來的漢繆篆時,其圓勻婉轉、舒展流暢被平方正直、渾厚敦實所取代,界格的平面審美意義就顯得多餘了,繼而逐漸退出實用印章的舞台。
1.2.2秦代政治、文化對印章規範化的要求是界格產生的外在動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戰爭兼并東方六國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大秦帝國。秦始皇為了鞏固自己的封建專制統治,稱帝立號,立百官之職,中央設九卿,地方設郡縣,有了完整的政治制度與政權機構。與此同時,秦朝出於政權統治和社會交往的需要,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等一系列的專制政策,以秦國小篆為標準,整合了紛繁複雜的六國文字。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印章作為官、私通行的憑信物也毫無例外,均被直接納入了統一規範管理。同文字一樣,秦代印章制度已經逐步形成了統一的官、私印製度:確立了秦代製作印章的標準書體,印材質地及形狀、大小有明顯規定,並以此來區分官吏的大小與等級。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吏由秦朝廷直接任免,隨官職所授予的印章則是其行使職能權力的重要憑證。秦代的私印,也逐步被官印所同化,顯示出一種秩序與井然。在秦代印章有着極其森嚴的等級制度,秦以前,無論官、私印都稱“璽”,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規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稱之為“璽”,臣民的印章只能稱之為“印”。秦代印章較之戰國璽印從形制上更加統一規範,形成了相對嚴格的等級制度。官印一般在2.3厘米見方,四字白文,“田”字界格,用摹印篆。下層官吏印章的尺寸則是普通官印的一半,即為2.4厘米×1.2厘米,二字(不包括重文)白文,“日”字界格,印文也用摹印篆,名曰“半通印”。秦印藉助界格形式使印面方正規矩、剛勁有力,盡顯秩序嚴整之美,充分體現了秦王朝法紀嚴明,強大統一之風。這是秦朝政治、文化對印章規範化的一種形式要求。蕭高洪先生在《秦印的特點及形成的文化背景》一文中認為“作為官印,它不僅是統治階級權力的象徵、取信的憑據,同時,甚至在其形制,文字的多寡等方面無不體現統治者的思想與意志,無不打上階級和時代的烙印,所有這些又貫串於中國古代印章發展的始終,這也是中國古代官印發展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 [1]可見,秦印選擇界格有着很濃厚的官方色彩,並非空穴來風。相對於官印,秦私印則顯得豐富多彩和生動活潑。基本上常見的幾何形狀都曾有發現,界欄、界格更加隨心所欲,自由發揮,如王駔、賈安、閻歐昫三方印章。(圖7、8、9)。私印文字取用範圍較大,既有復古的,用籀文;循規蹈矩的,用秦篆;也有新奇獵艷的,用秦隸,其規矩整合中的自由和秦權詔版文字的意趣則是非常接近的。

圖7

圖8

圖9
1.2.3施用載體——封泥的保密防偽是秦印選擇界格的內在技術保證
在紙張還沒有出現之前,印章除了是身份和權力的象徵之外,另一重要的用途是用印抑泥,封緘簡牘、物品等,後人稱之為“封泥”,亦稱“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遺迹。現在看來是蓋有古代印章的乾燥堅硬的泥團(遺存至今的封泥實物),原印多為陰文,鈐在泥上便成了陽文,其邊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寬邊。“封泥”的使用自戰國直至漢魏,直到晉以後紙張、絹帛逐漸代替了竹木簡書信的來往,“封泥”才退出了歷史舞台。
“封泥”的特殊性質要求字跡清楚,線條完整,便於識讀和檢驗,以防假冒和泄密。白文印章增加界格後,橫縱直線使抑壓在泥面上的文字輪廓更為清晰,印面文字更為聚攏團結,同時也增加了仿冒作假的難度。我們可以通過現在的技術手段來把帶有界格的“封泥印式”與去掉界格的印式進行一下對比(如圖10、圖11)圖10為秦封泥《左樂丞印》的原泥和墨拓稿,圖11為通過電腦技術手段在圖10墨拓稿基礎之上去除掉“田”字界格之後的效果,通過對比我們不難看出,去掉“田”字界格之後的封泥墨拓稿,顯得空曠了很多,四字之間顯得“各自為政”,字與字之間的聯繫驟然下降,與原稿相比清晰度也差了很多,秦代印章的嚴整秩序之美蕩然無存,同時降低了辨別真偽的難度。當前,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秦印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絕大多數均為帶有界格的陰文印,這可能和封泥之功用有着極其重要的關係。

圖10

圖11
由此可見,秦印選擇界格作為特殊的印式並非是茫然的、漫無目的的,而是根據當時的政治、文化對印章規範化的需要、秦篆文字的結構特徵及秦代印章的主要用途而“慎重”選擇的,是當時秦國官私印章歷史發展的必然。
以後的人帶來如此之高的審美愉悅。正是這種“無意於佳乃佳”的隨意性製作,在當時大量的印章製作過程中,我們的先人為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的藝術經典。
秦印“顫里典”[1](圖12),“顫里典”三字原有字形兩疏一密,若按 “顫”字占右邊半格,“里典”二字占左邊半格排疊,邊框線和界格就顯得有些多餘了。但此三字若按照圖12中章法排疊實在難以安排,眼前的界格邊框“”便是古人的發明創造了。“顫”在三字中筆畫最繁,但創作者並未格外施恩,反其道而行之,使之屈居右上角。正是由於“顫”字的緊縮取密集裝,方使“里”、“典”二字因筆畫少與之形成繁簡、虛實的對比參照,從而界格便有了存在的價值。“顫”字為了增加合力,其左右部件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位移,以適應這個變化要求。左上人字頭作左撇右捺狀,上中部連接的短豎向右偏移至捺的中部,使捺的中部隆起作反捺狀。右“頁”部上端昂起,上部上大下小,左上和左邊中部右肩相連,中腹二小短橫較細,左高右低。中部右邊和右邊框泐損貫氣。最妙的是“頁”部下腳偏左上提,其人字形作左反撇又捺,和左上的人字頭作粗細、方向、線形的對比變化呼應。“里”字居印之右下,上提偏右安排。由於獨體字“里”字里沒有斜線的穿插,其橫豎線的交接碰撞愈見其妙!“里”字“田”部左豎線向左彎曲和右豎線稍稍向左彎曲並和上界格線相接,但並未衝過界格線。“田”部中橫的下沉和“土”部短橫的上提,人為地增加了“里”字中宮的分量。中豎線明顯的偏左安排,刻意地增加了向左靠攏的意願,增強了印面的團聚力。“典”字筆劃雖少卻獨佔兩字空間,重心居下上部留空排疊。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典”字第二條橫線和右邊界格線的連接,若是作者有意為之,更加讓人嘆服;若是後天的泐損所致,真可謂鬼斧神工不可及。使原本“”的界格形狀變成了十字交叉的“田”字形界格,居然化解了三字印章出現的不相稱感。此處界格已經成為印面藝術效果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界格的巧妙應用為本難以安排的三字印式增添了無窮的藝術情趣和審美價值,堪稱秦印界格之典範。

圖12
秦官印“左礜桃支”(圖13)因為界格的存在,才使其在章法上形成了如此強烈的對比,上緊下松,左疏右密,饒有興趣。界格的劃分是印面中最醒目的章法分界線,可以直接確立章法格局,它對印面視覺效果的影響堪稱巨大。
秦代私印多為鑿印。相比秦官印而言,秦私印更加燦爛多姿。無論是從形制上還是章法布白及意趣上都顯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浪漫氣息。其形狀有方、長方、圓、橢圓等多種。印面加有界格。無論何種形狀,印文都能隨遇而安,處理得極為和諧統一,顯示出高超的應變技巧。
秦私印“上官郢”(圖14),三字每字各居一格,筆劃繁簡不一,格線依三字繁簡程度略有大小之變,避免了三格等分的單調。文字結構造型各具其態:第一,依分格形狀各自而居,“上”字頭頸曲上,拱身其腳以左高右低而斜坐;“官”字則盤坐於斜屋頂之內;“郢”字則微微躺睡。第二,從全印章法看,“人”形中心點,似為圓心,若以長度為半徑圓,有不安定之感,而此處“人”字形,其身豎直,兩腿分開,又感到非常平穩。構成圓中有方、不穩中寓穩。第三,在筆劃變化上,是方圓並存,直弧相襯,如“官”字“宀”部圓意多、而下半部分則方意多。“郢”字中“呈”部之“口”與“邑”部之“口”則各方圓並置。直線和弧弧線、方與圓的相間組合,產生了圓熟與生辣的對比關係。三字能夠如此妥帖地排疊在一起界格線所起的作用首當其衝。
秦半通印“李朝”(圖15),“日”型界格線的巧妙布施使此印從上到下,通篇洋溢着輕鬆愉快、天真爛漫的氣息,給人以美的享受。尤其是“日”字中間橫隔線的傾斜最為巧妙。不僅為居上的“李”字爭取到更為廣闊的天地,而且擠壓下邊的“朝”字,使其必須作出適應性的變化和勢的支撐。“朝”字左下“十”部的橫線是全印中唯一未作傾斜的一條橫直線,此橫線為“朝”字在傾斜中保持平衡、協調此印整體章法立下了汗馬功勞。
秦印具有繼往開來的鮮明時代特徵,以字態修長、方折挺直、圓勁遒媚類似於權量、詔版上的文字最為特色。較之戰國秦國古璽印風格統一而嚴整,文字遒勁而安詳,章法整飭而從容,其獨特風格足以令後人傾倒。秦印選擇界格是和當時的歷史、文化環境、用途及秦篆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看似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其實不然,界格的出現為等級森嚴、規整有序的秦印也帶來了無窮的“歡樂”,其在確立章法格局、強調印面形狀和秩序、突出印文體勢等諸多方面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秦印選擇界格即是歷史文化環境的抉擇,也是當時藝術審美情趣的選擇,秦印之於界格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亦是審美追求的必然。

圖13

圖14

圖15
2.2印章史上界格印式的淡化
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翻滾,時至西漢,此時的官印和私印基本都沿襲了秦代舊制,有邊欄和界格,入印文字主要還是小篆,但此時的小篆體勢不及秦印圓轉,而以方為主,寓圓於方。西漢中期以後,印章基本上不再採用邊欄和界格的印式,文字上更趨於平直和方正,整齊端莊。如果說秦印選擇界格作為其印式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那麼在隨後的千百年間界格又淡化在後續時代的印章體系中,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遂命令李斯、趙高等人進行文字統一工作。在形成秦小篆這種官方正式文字的同時,民間也在悄悄地進行一種俗體的“文字變革”,這種變革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直至隸書日臻成熟,史稱“隸變”。小篆由於字體修長、結構複雜、書寫工整、書寫速度較慢,給日常書寫工作帶來極大不便。在這種情況下民間逐漸形成一種書寫相對便捷、書寫速度較快的“俗體”字——“隸書”。據現在考古發現,在戰國晚期就已經出現了“隸書”的萌芽,由先秦戰國到西漢前期為初創階段,被稱為“秦隸”,而由西漢後期到東漢為成熟階段,被稱為漢隸。“隸變”是中國漢字發展史和書法藝術發展史上一次卓越的革命,突破了單調、拘謹、細圓、均勻的繪畫線條,生髮成輕鬆活潑、任情恣肆、粗細不等的書寫線條,進而表現出漢字結構特有的豐富姿態。文字形態由小篆的縱向瘦長趨於橫向扁方,線條也開始圓中寓方。
根據事物演變和發展論的規律,我們不難看出任何一種新生事物或意識形態的產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個逐漸衍變的過程的。由秦印向漢印演變的過程亦不例外。“文字的演變影響和決定了印章的發展,影響了印面形式的變化。秦印中一些工整之作如‘旃郎廚丞’(圖16)、‘邦侯’,(圖17)還有近年出土的大批秦封泥中的諸多工整作品,它們在細節上已經具備了相當多的漢印技法特徵。漢代印章初始依然沿襲秦印舊制,西漢早期的印章部分還仍帶有界格,但此時印中的界格已逐漸失去在秦印中所具有的作用。如西漢早期印章‘文帝行璽’(圖18),文字仍還有部分作圓筆處理,但較之秦印文字更加趨於方正平直,秦印中那種自然活潑之趣也在逐漸減少。到西漢中後期,政治、文化等各種制度都趨於定型,印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印文趨於方整,筆畫屈曲飽滿。至西漢晚期,官私印印章已具備性格強悍、特色鮮明的‘漢印’格式,以渾厚典雅為主流漢印風格逐漸形成,繆篆已成為其特有的入印文字。由於繆篆外輪廓的平方正直,外部空間結構趨於靜態,界格的規範壓縮功能接近於零,退出印章史的舞台就成為必然了”[1]。“界格的演變乃至退化主要還是因為入印文字的演變。界格的退化是與入印文字的有序化同步的”[2]。界格形式是古璽、秦印不規整印文與方形印面形式融合的依託,但不論是他們當中有界格的作品日趨方整還是一些超前的無界格作品,都在預示着脫去界格的明顯趨勢。

圖16

圖17

圖18
在隨後的魏晉南北朝以至唐代這段漫長的實用印章時期,界格依然悄無聲息的被後人所遺忘。大約在宋元至明代中期,文人開始介入印章製作。從文人篆印請工匠代刻到自篆自刻,篆刻藝術開始逐漸成熟。在篆刻藝術形成的初期,界格這種印式依然被人們遺忘在印章史的某個角落。
由原始走向成熟,由無序走向有序是歷史的必然。界格淡化在後續時代的印章體系中也是歷史的必然。
3界格印式在篆刻創作中的廣泛使用[1]
篆刻藝術生髮於古代的實用印章。數千年來古代印章在以實用為目的的製作之中,派生出了篆刻藝術之美。時至今日,篆刻已經成為一種彰顯華夏民族豐厚文化底蘊的重要藝術形式。濃郁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後世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藝術樣式,奠定了篆刻藝術語言的基調。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是在繼承中求發展的,沒有一種創新能夠完全脫離傳統,汲古方能出新,篆刻藝術更是如此。
界格印式作為印章史中一種特有的樣式,在淡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又被無數的篆刻家所重視所景仰,以此為創作基調,繼承古意、揉合己意、生髮新意,創作出一件件精彩至極的篆刻藝術作品。
清代篆刻家吳讓之早年師從鄧石如的學生包世臣,作為鄧石如的再傳弟子,其是“印從書出”理論的積極踐行者。他深知書法對篆刻的重要性,故其非常注重書法修為的提升,並取得了頗高的造詣。吳讓之主要以小篆入印,其書小篆經過“印化”稍稍帶有一些漢篆的味道,但又輔以大量的圓斜筆畫,恰好與秦界格印式廣博的包容性相吻合,使得吳讓之這種界格印式的創作如魚得水。如“岑鎔私印”(圖19)、“仲陶”(圖20)二印,方直的界格線與秀美的吳氏篆書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加上吳讓之獨具特色的篆法、刀法、章法,形成了一種特色鮮明的創作風格。

圖19

圖20
西泠印社首任社長缶翁吳昌碩是最善於借鑒秦印式進行創作的高手,但其與吳讓之的風格又截然不同。吳昌碩以生辣勁健的石鼓文字入印,取法廣博、涉獵寬泛,再加上大師級的藝術秉賦和情懷,營造出了一種氣息高古、渾穆生辣、“老樹著花無丑枝”的創作風格。其朱文印“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圖21),“生於”二字用作合文,本來十字的印文作九字排列,字與字之間施以界格,但每個字又不受格線約束,在平衡中又彰顯出不拘一格的意趣。字體筆意豐滿,施以粗細、圓潤、合文、並筆等手段,使得整個印面渾古明麗。仿封泥印式進行創作的朱文印“翊印”(圖22),氣息酣足,技法純正,又不失自我。白文印“倉碩”(圖23)界格的布施更見精妙。左側借“碩”字“石”部左長豎為邊,右側無邊格,上下互見輕重和殘斷,信手拈來、古意盎然、無懈可擊。從秦印“日”字界格巧妙的演變成“工”字界格,大膽獨造,為我所用,非常人所能為也。秦界格印式在吳昌碩手中,樣式變化萬千,然又與缶翁篆刻風格和諧統一。

圖21

圖22

圖23
清代篆刻家黃牧甫的篆刻看似與秦印風格不合拍,但他對秦界格印式創作有着自己的獨到見解。“其白文印‘寄庵’(圖24)線條極見功力,即整飭又恣肆。這二者本來是相互矛盾的,但在黃牧甫手裡竟能兼得。整飭在形,在於用刀;恣肆為骨,在於結字。‘日’字界格按照常見的樣式根據印文筆畫的繁簡進行空間劃分,‘寄’字方正居中,而庵字向右偏移,左邊留空,加之‘庵’字上部緊收使之左右自然留白,‘庵’字透露出平中求變的訊息。‘日’字界格中間一橫線,為了避免獃滯,與右豎格線在交接時稍稍衝出一點點,煞是精妙,在不動聲色中完成整印。又如黃牧甫仿秦印中的圓形界格印創作的兩方‘崇徽’(圖25),圓形印的文字隨行布局,又有自己個人的一貫風格,二者怎樣調和是關鍵所在。黃牧甫運用了一靜一動的處理方式,‘崇’在兩印中都比較端正,只有在‘徽’字上做文章,讓其既保留自己的一貫印風,又要符合印章形式的的特殊性,使二者有機的結合起來。兩印非常成功,既有黃氏風格又有秦印古趣”。 [1]

圖24

圖25
湖南湘潭人齊白石的篆刻以大刀闊斧、酣暢淋漓的創作風格將傳統的篆刻藝術以嶄新的面貌帶入現代社會。從表面看,貌似齊白石方正的字形結構和挺拔、勁直的線條與規矩、整飭的界格線相互矛盾,與秦界格印式格格不入。但是如果我們透過表面仔細推敲齊白石的篆刻作品,其以直、斜線為主的線形結構,置放於界格印式之中又別有一番風味,有着他獨到的施用方式。如八字白文印“以農器譜傳吾子孫”(圖26)和五字印“老手齊白石”(圖27),界格線均以傾斜恣肆的形態出現,界格線所分割出的塊面大小各異,不平均的排疊巧妙的化解了方正的文字與界格的矛盾衝突;其次,齊白石印中文字不受界格所限,施以並筆、破邊、衝破界格等手段,營造出大疏大密的章法空間,給印章帶來了靈動、精彩的視覺衝擊。膽敢獨造的齊白石巧妙地化解了文字形態與界格之間的矛盾,讓自己印章中的界格完全服務於齊氏文字和章法。

圖26

圖27
當代已故江蘇篆刻家馬士達的篆刻藝術充分張揚人的自由精神,不以形累神,而以神鑄形。其作品以獨特的風貌、奪目的效果和強烈的藝術個性顯赫於當代印壇。馬士達先生在談到印宗秦漢時說“以心法宗秦漢,就是要體悟到‘自由則活,自然則古’這條根本的藝術規律。作為篆刻藝術的本源,古璽、漢印是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並從中汲取營養的藝術原型,但是對原型的把握與轉換,決非只意味着對形的摹擬與仿效,或者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的對‘神’的泛談,最重要的莫過於對古鉨漢印的藝術精神的領會與表現”。[1]馬士達先生之於秦印界格印式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不是對形簡單的模擬和效仿,而是對秦界格印式這一藝術精神的領會與表現。其白文印“方令儒印”(圖28)中所用界格由傳統的“田”字格演變而來,根據自己的審美理念調整至現在的界格樣式。界格在馬士達先生刀下只是自己營造虛實、調節氣息、布白印面的一種手段,通過強有力的視覺衝擊達到氣息酣暢,形神兼得才是其所追尋的根本目的。印作“程大利印”(圖29)巧借不規矩的“口”字型界格樣式,營造出顯著的疏密效果及不同凡響的藝術效果。馬士達先生的篆刻從秦漢印中來但不拘泥於傳統,有着自己的獨特面貌和審美情趣。

圖28

圖29
當代篆刻家王鏞的篆刻取法多樣,汲取古陶刻、古璽、封泥、磚瓦文字等諸多元素,入印文字多樣化,營造出一種樸厚野逸的篆刻語言。王鏞先生的篆刻作品是耐人尋味的,初一觸目,一股樸厚之氣迎面而來,但其中所隱含着的理法和味道非常人立而可識,而需要慢慢咀嚼方曉其中之佳味。其朱文印“勇於不敢”(圖30)和“攻玉以石”(圖31)以秦漢磚瓦文字入印,藉助界格印式的表現形式,施以渾厚樸拙的用刀,創造出一種簡潔明快而又樸厚、勁爽、簡約的自家印風。

圖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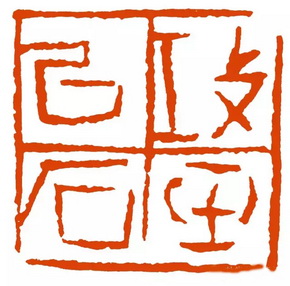
圖31
由實用印章到文人篆刻的興起,篆刻藝術經過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逐漸積累了豐富的藝術表現形式、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內蘊。界格印式作為一種印式也歷經了千百年的流傳和演變,發展至今已和最初的功能和形態有着太多不同,這是歷史的必然亦是時代的進步。與時俱進,是當下社會賦予每一個藝術工作者嶄新的時代使命,如何做到汲古出新,將這種傳統的藝術形式發揚光大,是擺在每一個藝術工作者所面前的歷史使命。界格印式只不過是篆刻家創作過程中的一種創作元素,不同的篆刻家按照自己的審美理念和創作風格賦予其各不相同的生命形式,又讓其完全服務於篆刻家自己的藝術秉性和審美理念,在不同的篆刻家手裡卻又有着千變萬化的形態。
結語
從目前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那三方“商代璽印”到今天彰顯出繁榮景象的篆刻藝術,印章由最初的實用價值逐步登上了純粹的藝術舞台。秦界格印式在經過歷史和篆刻藝術家們無數次的考驗和選擇之後,才逐漸顯示出其在幾千年印章史中的審美價值。
最初,界格是秦代印章印面劃分的一種特有表現形式,並成為印章史上辨別秦印的一個重要的標緻性符號。本文通過對秦之前璽印界格印式的分析和秦印選擇界格印式的必然兩方面對界格印式作了系統的分析和論證,進而得出秦印界格產生的三方面原因:秦篆文字的形體特徵是界格有無的內在動因;秦代政治、文化對印章規範化的要求是界格產生的外在動因;施用載體——封泥的保密防偽,是秦印選擇界格的內在技術保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秦印選擇界格即是歷史文化環境的抉擇,也是當時藝術審美情趣的選擇,秦印之於界格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亦是審美追求的必然。
當歷史的車輪行進至漢代,漢字經過“隸變”的重大變革,原本以縱向取勢的秦篆文字被以橫向取勢的隸書所取代,從而成為這一時期官方的主要書體。到西漢晚期,以渾厚典雅為主流的官、私印印章已形成特有的“漢印”格式,外部輪廓平方正直的繆篆已成為其特有的入印文字。此時的繆篆外部空間結構已趨於靜態,界格原有的規範整飭功能已經發揮不出作用,退出印章史的舞台已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當實用印章逐漸轉變為文人所青睞的文房雅玩,並進而成為一門能夠彰顯華夏民族豐厚文化底蘊的重要藝術形式之後,其創作開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秦界格印式作為印章史中一種曾經特有的樣式,在淡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又被無數的文人篆刻家所重視所景仰。他們通過自己對篆刻藝術的認知和理解,在秦印界格印式的基礎之上,繼承古意、揉合己意、生髮新意,創作出一件件精彩至極的篆刻佳作。以秦界格印式為創作基調的印風又迎來了在印章史中的另一個春天,再次凸顯出其在印章史中不可或缺的審美價值。我們現在來探尋秦印界格在印章史中的審美價值,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的篆刻藝術。我們期待更多的篆刻家能夠了解、認識界格印式,並運用界格印式創作出更加精彩絕倫的篆刻藝術作品。
參考文獻
1.李剛田,馬士達主編.篆刻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
2.李剛田主編.中國篆刻技法全書[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8.
3.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先秦璽印[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3.
4.趙明.中國篆刻創作解讀古璽秦印卷[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2.
5.趙明.做印技法百講[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8.
6.趙明.古印匋、封泥代表作品技法解析[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7.許雄志.秦印技法解析[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8.許雄志.秦代印風[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9.許慎撰.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1日第一版,2001年3月18次印刷.
10.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1.沙孟海主編.印學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
12.葉一葦.篆刻叢談[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
13.葉一葦.篆刻叢談續[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
14.谷松章.篆刻章法百講[M]. 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15.王人聰.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C].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2000年出版53頁.
16.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7月第6次印刷.
17.孫向群.老驥伏櫪-馬士達藝術生活訪談錄(J).東方藝術書法,2008,(21):56-70.
18.蕭高洪.秦印的特點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J).江西文物,1990,(3):83-86.
19.張冬煜.秦印與秦陶文(J).西北大學學報,1999,(2):118-121.
20.牛濟普.秦印瑣記(J).中原文物,1988,(4):63-71.
21.王輝.秦印探述(J).人文雜誌,1993,(6):236-251.
22.許雄志.秦印章法特點解析(J).青少年書法(青年版),2007,(1)20-23.
23.王振波.芻議秦印界格(J).書法,2010,(8):34-36.
24.王振波.淺析界格在印章史的審美意義(J).文藝生活,2010,(05):52-53.
學習交流微信號:wenbaozhai365


